(2017年6月21日,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剑河县南明镇,台沙村第一书记杨精泽在下村开展民情访问归来途中。图/中新)
第一书记的乡村治理
本刊记者/黄孝光
发于2020.12.7总第975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

9月末,经历了六年三任第一书记的接力脱贫攻坚,四川凉山美姑县热口阿觉村即将迎来最后的验收时刻。
压力层层传导,最终落在以第一书记为主导的驻村干部身上。脱贫成果来之不易,热口阿觉村的第一书记王诏越来越忙,他不希望在验收时出现丝毫差错。迎检之前,王诏组建了30多人的妇女团队,对各家衣服摆放、被子折叠、卫生状况等进行检查指导。村里的彝帽编织队伍也就位了,以向验收人员展示他们独特的手艺。迎检前一天,王诏还熬夜把23卷脱贫资料重新核查了一遍。
王诏是今年1月就任的热口阿觉村第一书记。2018年6月,四川在全省范围内选派3500余名帮扶干部,驰援凉山11个深度贫困县。任职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五分局交警的王诏主动报名,成为美姑县腾地阿莫村的驻村干部。腾地阿莫村脱贫后,表现突出的王诏被调任至热口阿觉村。热口阿觉村海拔2200米,直到2018年才通上公路。脱贫任务更加艰巨,全村219户964人,王诏去时尚余贫困户78户390人。
这是一场举全国之力的战役,其动员力度之大,投入成本之高,涉及人员之广泛,前所未有。截至2020年3月,全国向农村社区共派驻了25.5万个驻村工作队、290多万名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,仍在驻村的有91.8万人。脱贫攻坚促成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大规模的干部下乡。
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,中国即将消除绝对贫困,进入后脱贫攻坚时代。全国农村工作重点如何由精准扶贫转向乡村振兴?第一书记制度向何处去?成为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不得不考虑的重大议题。
(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牛牛坝乡,热口阿觉村第一书记王诏 (身着浅色警服)和同事在向村民散发禁毒防艾的宣传单。图/受访者提供)
“平战结合”的驻村队伍
“全国脱贫看四川,四川脱贫看凉山,而美姑县是凉山贫困面最广、程度最深的一个县。”王诏说。
国家规定的贫困户脱贫标准为“一达标两不愁三保障”,四川将其进一步提升为“一超六有”——年人均纯收入稳定超过国家扶贫标准且吃穿不愁,有义务教育保障、基本医疗保障、住房安全保障,有安全饮用水、生活用电、广播电视。“一超六有”中,个别指标容易生变,给脱贫验收带来不确定性。为此,美姑县成立了专班来应对电视信号消失等突发情况,王诏则筹集了十余台电视,以防有贫困户家电视临时损坏而影响验收。
截至今年2月底,中国贫困县从832个减少至52个,其中有7个在四川凉山。这些剩余贫困县被中共中央总书记、国家主席习近平形容为“贫中之贫、困中之困”,是“最难啃的硬骨头”。
根据相关要求,符合退出标准的贫困县需在当年9月底前提出申请,9月30日成为凉山7县摘帽大考的最后期限。以9月30日为脱贫年度节点,凉山各地挂出迎检倒计时的标语,王诏所在村亦贴出“倒排工作表”,“每个月排一次,精确到每周甚至每天要干什么工作。”
相比之下,500公里之外的贵州六盘水,同样驻村在深山区的苏维压力小了不少。今年年初,贵州尚余9个贫困县未摘帽,其中位于乌蒙山腹地的六盘水市有3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、1个省定重点县,2014年建档立卡时贫困人口占了全市人口的五分之一。2015年,六盘水市质监局办公室主任苏维主动请缨,到全市贫困发生率最高的水城县阿戛镇高中村(后并入电光村)当第一书记。彼时高中村共374户2056人,贫困户258户1405人,贫困发生率高达68.33%。而到今年年初,该村贫困发生率下降到1.51%,仅剩21户贫困户。
作为2014年全国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最多的省份,贵州将脱贫工作放在第一位的高度,明确提出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。六盘水市扶贫办副主任张树才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中央要求扶贫工作省、市、县、乡、村“五级书记一起抓”,为此,六盘水市委市政府每年与县区、市直部门层层签订责任书,逐级立下军令状,形成了五级书记一起抓扶贫的工作格局。进入2020年,干部派驻力度逐步加大。据张树才介绍,脱贫攻坚以来,六盘水全市368个市、县直机关单位结对帮扶547个贫困村,5.8万名各类帮扶干部实现对15.8万户61.6万贫困人口结对帮扶全覆盖。
(2019年7月3日,广西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杆洞乡,锦洞村第一书记韦斌(右)坐三轮车下村。图/新华)
脱贫攻坚堪称一场浩大的政治动员,从中央到地方,各级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都明确了定点帮扶任务。2015年4月,中组部、中农办和国务院扶贫办印发《关于做好选派机关优秀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工作的通知》,要求对全国12.8万个贫困村和57688个党组织软弱涣散村选派第一书记开展驻村精准帮扶,此后第一书记制度全面铺开。全国在岗的91.8万驻村干部中,第一书记有逾20万人。以贵州六盘水为例,第一书记的来源包括中央、省、市、县、镇5个层级,550多名第一书记实现了对贫困村和非贫困村的全覆盖。
作为“五级书记抓脱贫”的末端,驻村第一书记是这场脱贫攻坚战役的重要角色,深度参与村庄规划、产业布局、招商引资等扶贫事宜。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学者黄丽芬自2017年开始对第一书记进行持续调研,在她看来,第一书记制度相当于中央和地方政府各项“三农”政策和惠农资源的村庄集束器。“精准扶贫以来,来自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各种政策、资源、项目、理念大幅度输送至村庄,第一书记群体作为扶贫主体与之同步进村,为实现国家与村庄、政府和农民的有效对接提供制度化渠道。”黄丽芬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分析。
不同类型村庄,派驻什么类型的第一书记有一定的讲究。“总体而言,是把最难啃的骨头交给最有能力或实力的人。”据黄丽芬观察,更高的层级、更核心的部门所派驻的第一书记,去的往往是贫困程度更深的村庄。
实践中的做法更为细致,据六盘水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吴国兴介绍,当地在选派第一书记时,首先组织相关部门对贫困村进行摸底,逐村了解情况,把所辖村庄分成基层组织建设薄弱的“弱村”、社会矛盾纠纷突出的“乱村”、经济发展滞后的贫困村等类型;其次摸排各单位符合条件人员,了解其专业特长、工作经历、家庭情况等;在此基础上进行人村匹配,比如党政干部匹配组织建设薄弱村、政法干部匹配纠纷突出村、经济干部匹配发展滞后村等。
吴国兴举例说,六枝特区关寨镇是市级极贫乡镇,地域偏远,群众思想固化,村落之间矛盾纠纷较多,为此他们安排了市公安局4名干警到该镇担任第一书记。水城县阿戛镇电光村90%以上村民为苗族,且多数村民听不懂普通话,为此组织部门选派了熟悉苗语的苏维赴任。“事实证明,他去以后能短时间融入群众,迅速打开工作局面。”吴国兴说。
第一书记并非“孤军深入”,而是以团队的方式进村。六盘水市驻村扶贫人员通常包含5大类型:一是第一书记及驻村工作队,按省委组织部要求,一般由5人组成;二是结对帮扶干部,确保每户贫困户都有一名公职人员帮扶,视实际工作需要下村;三是下派轮战干部,由市、县选派单位领导班子成员,进行每人驻村时间不低于1个月的帮扶;四是下沉干部,相关单位除轮战干部外,还会另派数人到村子支援,在村时间数月不等;五是决战工作队,由乡镇副科级干部担任队长,第一书记、村支书担任副队长,统筹在村工作帮扶力量,开展脱贫攻坚工作。
杨波2010年来到六盘水市钟山区海嘎村,连续驻村11年,是贵州驻村时间最长的第一书记。他告诉记者,海嘎村目前有驻村队员5人、轮战队员1人、下沉干部4人、村两委干部10人,此外相关单位还会阶段性选派补充力量。“包括村两委干部在内,一个贫困村通常有20人左右的干部团队。”六盘水市扶贫办副主任张树才说。
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小云在接受《中国新闻周刊》采访时表示,过去多年的社会转型过程中,贫困乡村大量的智力资源流失了,很难组织村民承接脱贫攻坚的各种任务。在这种情况下,大量补充第一书记这种人才资源,对做好脱贫攻坚尤为关键。
(2020年1月6日,广西河池市大化瑶族自治县板升乡,八好村驻村第一书记韦德王(左)和村干部去贫困户家里走访。图/新华)
从“娘家”到“婆家”
2015年刚到高中村时,在农村长大的苏维仍然感到震惊:“这个地方完全超出我对贫穷的想象!村里没有信号,村民喝的是雨水。电压也不够,有一家用电磁炉,其他几十户就用不成电了。”
高中村十几个寨子分散在高山深谷,苏维到任那天,村庄被雾气笼罩,看不到人家。村道均未硬化,他花了3个小时才走到村委会。
“我那情况也差不多,村民背点土豆去集市卖,来回就要走8个小时。村里流行这样一句话:点着火把出去,点着火把回来,走到半路天才亮,回到半路天都黑。”海嘎村第一书记杨波说。
交通闭塞严重阻碍山村经济的发展,为此,几名受访第一书记不约而同地通过修路、完善基础设施来打开工作局面。杨波修路的第一笔资金是向其派出单位钟山区委统战部、区民宗局申请而来的。此前媒体报道,自2011年以来,杨波不断从派出单位争取少数民族发展资金、少数民族“双培”资金等各类项目资金近180万元。借助这些资金,他逐步修通了村里的通组路、串户路,安装太阳能路灯,并解决了移动信号覆盖问题。
在定点帮扶机制下,驻村第一书记的派出单位是所驻贫困村的帮扶单位,其能提供的资金、项目、技术、人力等资源是第一书记帮助贫困村脱贫的重要保障。“不少第一书记将派出单位称为‘娘家’,将村庄称为‘婆家’。能否在‘婆家’取得优秀业绩,很大程度上取决于‘娘家’本身实力和支持力度。”学者黄丽芬向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表示,“娘家”单位的资源能力和政策力度,是影响第一书记资源网络的关键。资源能力越强的单位,派驻的第一书记向村庄提供的帮扶越大。
苏维的“娘家”是六盘水市市场监管局。“虽然资金实力不如其他部门,但可以随时给我协调全国各地的技术专家,这是我‘娘家’的优势。”据苏维介绍,得益于六盘水市市场监管局在企业管理、种植技术、生产方式等方面的支持,他在高中村成功实施了多个产业项目。
苏维探索的第一个项目是养牛。“这里的苗族村民非常喜欢黄牛,村里荒山也多,养牛是发展产业的第一选择。”2016年年底,在村委会牵头下,42户贫困户参与成立水城县“牛得很”农民种养殖专业合作社,按照“统一管理、集中养殖、自主经营”的模式,以“公司+合作社+贫困户”的方式进行。
(2020年11月初,贵州六盘水市水城县阿戛镇,电光村第一书记苏维介绍养牛产业情况。本版摄影/本刊记者黄孝光)
“建筑人员来看后,绘了两个养牛场的图纸,说要花500万元。我们没有钱,就开动员会,让群众先把地免费租给合作社,并让每家每户出义务工。最终花80万元完成施工,加上买牛钱,一共花了130万元。”在“娘家”的帮助下,苏维邀请专家进行养牛技术指导,并带合作社成员到省内20多家养殖场学习取经。看到养牛场产生效益后,越来越多的群众主动申请加入,苏维申请到产业扶贫资金400多万元,将养牛场规模扩大到1万平方米,可养殖1000头牛。
驻村帮扶中整合的资源实际上是系统性的,除“娘家”外,从乡镇政府、各个部门到社会力量,均构成第一书记的庞大后援团。以乡镇政府为例,其拥有精准扶贫资金配置、项目审批的权力。“资源是有限的,蛋糕怎么分是个问题。第一书记是组织上派下来帮我们的,我们会尽全力去支持他们工作的权威性。”阿戛镇镇长宫熙提道。
2015年至今,高中村共争取项目50个,包括人畜安全饮水、道路交通、圈舍改造、危房改造、人居环境改造、文化及党建项目等,资金投入约6200万元。产业方面,在苏维主导下,高中村成功发展了集中养牛、牧草种植、少数民族服饰加工、火棘盆景等产业,建起了猕猴桃产业园、食用菌种植和黑山羊圈养基地。
学者黄丽芬曾撰文分析,进入村庄后,第一书记还会充分利用私人关系网络发动社会力量的支援,比如校友会、慈善机构、企业老板等。
资源如何得到有效利用,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第一书记的个人能力。高中村曾组织村民发展精品水果,但受海拔和气候影响至今未挂果,这让村民的积极性备受打击。为此,苏维在村中推广养牛业时困难重重,经过200多次动员会才将项目落地。“施工过程也是反反复复,我通知明早7点到工地,第二天去了发现一个人没有。也有不少村民投资后反悔,想收回资金的。”苏维表示,作为第一书记不能泄气,“如果有80%的成功几率,不能把20%表现出来,要表现出万分的信心才能把事干成。”
“让他们思想世界得到长大”
据学者罗兴佐观察,脱贫攻坚过程中,第一书记被赋予极强的资源属性,各方普遍认为,第一书记驻村核心目的在于带去资源。
“你去上头帮我们跑点项目就好,不用天天待在这里。”5年前,村支书和村主任对刚开始驻村的苏维说。据苏维描述,彼时高中村“没有一个高中生”,村民习惯于贫穷而抗拒改变,每到农闲时酗酒成风。时至今日,村中仍然张贴着劝诫标语:“不当懒汉不喝酒,早起干活早脱贫。”
2010年,刚驻村的海嘎村第一书记杨波同样手足无措。“因为大旱,民政部门运送爱心水,却无村民来领,跟我说除非送到家门口。不少村民家没有厕所,靠在灌木林里‘解决’,我告诉他们修一间厕所可以补贴400块钱,他们却跟我讲条件,说没有1000元修不下来。”
接连的挫折,让杨波明白思想脱贫的重要性。驻村11年来,杨波采取的是“引回来,走出去”的扶贫思路——既要吸引已经出去的、有见识的人回来建设家乡,更要鼓励村里的年轻人走出去。“我们这里属于‘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’,培育产业的同时,就业扶贫也很重要。而且年轻人出去锻炼几年,回来一口普通话,各方面都会有很大的提升。”
凉山热口阿觉村的第一书记王诏对此深有同感。一位村民16岁之前未离开过村庄,后来外出打工多年,学会了汉语,如今被王诏培养成村中唯一的致富带头人,在村中从事养牛业并协助扶贫工作。
为了鼓励村民外出务工,杨波经常给村民算收入账:“假设种十亩地,全家五口人干一年,收获土豆1万斤、玉米3000斤,收入大约1.2万元。但如果你家两个人去打工,一年就能赚7万多元。有个村民身强力壮,却害怕出去。我反复找他唠嗑,试图激起他内心的波澜,让他感受不一样的生活。”杨波说。
产业和就业扶贫之外,采访时杨波反复向记者强调,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关键点。“小手牵大手,通过对小孩的引导来改变家庭。他们长大了,海嘎才会迎来真正美好的未来。”为了讨好小孩,给他们灌输学习观念,杨波口袋里随时揣着糖果。每年儿童节,他都会给学生购买礼品,上台发言甚至表演节目。他向“娘家”和公益组织争取资源,向海嘎小学捐赠了桌椅、书本、校服、演出服等大量物品。2018年,他争取共青团贵州省委的支持,组织了15名学生参加省里举办的夏令营。
在驻村干部和学校教师的共同努力下,海嘎村村庄环境改善,海嘎小学也迎来巨变。“2010年我刚来的时候,村小只有一名老师、十几个学生,现在已经有12名老师、100多个学生了。”杨波提到,学校力推音乐教育,如今海嘎小学的学生人手一把乐器,有电吉他、架子鼓,“乐器将他们连向了外面的世界”。
(2020年7月1日,贵州六盘水市钟山区大湾镇,海嘎小学六年级“未知少年”乐队主吉他熊婷 (右)和其他成员在练习。图/中新)
今年8月19日晚上8点,海拔2360米的海嘎小学迎来高光时刻——11名女孩和新裤子乐队开了一场摇滚演唱会,142万人在抖音观看了他们的直播。“全村357户人,安了260多盏太阳能路灯,到了晚上一片祥和气氛。现在大家思维变了,会跟我说,以前的生活是不太行哦。”杨波说。
相比海嘎,凉山热口阿觉村的情况仍然艰难。王诏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村两委干部最高学历是小学毕业,唯一识字的村文书今年嫁人后和老公外出务工了。“没有驻村工作队,村里工作基本开展不了。”为此,王诏准备在11月末彝历新年,外出务工人员回家之际,补充招募一批新的致富带头人和村干部后备人选。在教育问题上,王诏同样下了很大功夫。“为了保证义务教育阶段零辍学率,在村干部需要逐户敲门,排查有没有漏掉或偷跑回家的。”
杨波认为,扶贫不光要修路架桥补水、争取资金建设项目,更需要注入新鲜理念,“让他们思想世界得到长大。”“起初他们不愿意往前走,或者不知道如何迈开脚步。等我们离开时,他们也能够行走自如,脱贫攻坚的目标才算真正实现。”
重塑乡村治理格局
有学者认为,为了完成脱贫攻坚的阶段性任务,代表国家治理的第一书记,在激活村庄社会“造血”功能的同时,也给原有的村民自治秩序带来了改变。为此,第一书记需要处理好“国家治理”和“村民自治”的关系,一方面发挥国家的规划、引导、帮扶作用,另一方面发挥村民的主体作用和积极性。
“第一书记发挥的作用很大。”六盘水市扶贫办副主任张树才向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提道,中西部地区发展滞后,与村干部素质欠缺有莫大关系:“村两委干部祖祖辈辈在那里,资源、思维包括工作方式有很大的局限性。第一书记熟悉村情以后,很容易施展其统筹协调的才能。”
苏维的实践印证了这一点。“我在省、市、县直机关都待过,但对国家惠民政策如何落地见效不了解。到高中村后,我才明白从中央到地方,政策是怎样最终落地的。”苏维认为,第一书记一职给予其充分的发挥空间。
如何处理与村两委的关系,是苏维等第一书记必须面对的问题。根据学者黄丽芬的研究,围绕扶贫工作,第一书记和村两委形成了三种关系形态:包办代替型、辅助合作型和独立松散型。具体而言,包办代替型关系指的是第一书记掌握村庄多项事务的决策权,替代村两委成为实际的“当家人”;独立松散型关系指的是,第一书记在村庄发展中未能发挥明显作用,村民更认同村干部。
相较之下,辅助合作是较为理想的关系形态——第一书记和村两委之间建立起高效有序的分工合作关系,共同推动村庄的发展。“为解决好两者关系,我们主张第一书记下去过后,哪怕职级再高、能力再强,也要服从乡镇党委的统一领导。在帮助建强基层党组织的同时,避免大包大揽、打乱基层脱贫攻坚工作的指挥体系。”六盘水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吴国兴说。
辅助合作的关系需要着力培养,而这也是第一书记角色的题中之义。相关文件明确指出,第一书记驻村包含四大工作方向:组织建设、精准扶贫、为民办事服务和提升村庄治理水平。这意味着,发掘并培养一支高度团结、战斗力强且“带不走”的村委班子,是第一书记的首要职责。
苏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增强村两委的治理能力。他和村干部一起研究制定新的规章制度,要求村干部实行坐班制并纳入考核报镇政府;探索“组村社合一”,村党支部与合作社合署办公;2017年村两委换届选举时,他还积极做工作让文化程度低、年纪较大的村干部主动退出了村两委。
杨波采取的则是“人为掉链子”的方法。“我们把机关办公先进之处引到村里,教村干部打字、整理材料。为了提高他们的办事效率,避免他们产生依赖,有时候我就故意在任务紧的时候头疼一下、肚子疼一下,逼迫他们走上前台。”据杨波介绍,海嘎村两委如今成了“微型政府”,纪律严明,每天按点上下班。“上面千条线,下面一根针。无论脱贫攻坚、综治维稳、疫情防控、扫黑除恶、防汛防灾等,都是我们这一帮人在做。我们实行的是‘小分工大合作’,白天工作,晚上会议调度。大家一荣俱荣,一损俱损,是一个战壕的兄弟。”
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杨芳撰文提到,驻村第一书记政策的实施,不仅助力脱贫攻坚,也改变村庄治理的模式,形成国家支持、村委主导、村民参与的新的村庄治理格局。
苏维认为,脱贫攻坚以来,村民对国家政策的理解和支持发生了逆转。“曾经一段时间,干群关系紧张,村干部觉得群众蛮横无理,群众觉得干部不干实事。”苏维将村庄治理比作谈恋爱,是干部和群众互相建立信任、达成默契的过程,“‘单相思’没用,上面搞某个政策,不是直接就能落地实施。尊重群众的想法、意愿,把方法、思路变成群众自己的很重要。”
(2020年9月30日,山东淄博市沂源县东里镇,大沟村第一书记徐计划骑行在去往村里工作的路上。图/中新)
从集团军到特种军
六盘水市扶贫办提供给《中国新闻周刊》的资料显示,截至目前,该市62.66万贫困人口已全部脱贫,贫困发生率由2014年的23.3%下降为0,615个贫困村全部出列,3个国家级贫困县全部“摘帽”。
杨波所驻的海嘎村不仅摘掉“贫困帽”,还成了韭菜坪旅游景区半山腰上的“花园村落”。宽阔干净的柏油路从山脚直通山顶,白墙灰瓦的民房错落有致,文化广场、卫生室、运动场等设施一应俱全。
脱贫攻坚即将收官之际,规模庞大的第一书记们也面临去留问题。作为脱贫攻坚战线上的年份英雄,明年是否会留在海嘎村,对杨波而言还是个未知数。热口阿觉村的王诏作为四川省综合帮扶队伍成员,则将于明年6月结束驻村工作。他希望离开之前为村里的集体产业做点事——将该村的彝帽编织手艺打造成特色品牌,把村中更多的闲置劳动力培养成手工艺人。
对贫困村而言,脱贫只是开始,乡村振兴的任务接踵而至。根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部署,乡村振兴以“产业兴旺、生态宜居、乡风文明、治理有效、生活富裕”为总要求,分三个阶段实施,到2050年全面实现“农业强、农村美、农民富”的目标。
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向《中国新闻周刊》分析,当前乡村振兴是低水平、起点式的,尤其脱贫攻坚重点所在的中西部农村地区,虽然农民脱贫了,地方经济基础却普遍比较落后。基于此,他认为当前阶段惠农政策的重点“不是要建设一个比城市好的农村,而是要建设一个能保持农村基本生产生活秩序、可以为绝大多数农民提供退路和保底的乡村”。
“对贫困地区来讲,扶贫和乡村振兴是一回事。”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小云向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提到,乡村振兴更加需要专业性的人才,更加需要充实村一级的党的领导;在这种情况下,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,其中一个环节是组织形式的衔接,而第一书记制度是组织衔接中最重要的部分。
(从乡镇领导到驻村干部,阿戛镇建立了系统的脱贫攻坚组织架构。)
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,要将第一书记制度向乡村振兴任务重的村拓展,促使第一书记与脱贫攻坚、乡村振兴实现衔接。这意味着,将“建立第一书记派驻长效工作机制”。今年脱贫攻坚相关会议中,中共中央总书记、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多次强调,“要把贫困群众‘扶上马’之后再多‘送一程’”“严格落实摘帽不摘责任、摘帽不摘政策、摘帽不摘帮扶、摘帽不摘监管的要求”。
而如何实现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无缝对接,成为继续推行第一书记制度的关键议题。
“据了解,中央政策对西部地区脱贫攻坚有个过渡期的说法,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前5年重点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,保持政策相对稳定,在此基础上适当进行优化调整。”六盘水市委组织部二级调研员廖明芳向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表示,脱贫攻坚属于集团军作战,需要的是擅长搞攻坚、能猛冲猛打的干将,乡村振兴阶段需要的则是特种作战,倾向于选拔会经营、懂产业、擅管理的小诸葛式的人才,“人数不一定要这么多,但专业能力要强。”
苏维认为,乡村振兴过程中,核心依旧是发展产业:“不能指望靠村民打工回来建设家乡,也无法完全依赖国家施惠。解决不断依赖向上要钱的唯一途径,是增加村集体的收入。”据苏维介绍,为避免吃“大锅饭”的弊病,电光村正在对村合作社进行改制,将村民股份转给有企业经营管理能力的大户,由大户经营并每年分红给村委,村委再将利润分配给前期投资的村民。
学者黄丽芬认为,当前由精准扶贫向乡村振兴过渡的阶段下,第一书记工作重心应放在如何实现从造血到输血的转变上,回归到村庄组织建设上来。“无论贫困治理还是乡村振兴,真正的主体应该是村干部和村民,提高村庄内生社会活力和治理能力,是第一书记工作的最重要方向。”贺雪峰则向《中国新闻周刊》强调,扶贫攻坚结束后,基层治理应尽快恢复常规。
“在省里规范制度出来之前,我们这里下一步的乡村振兴将沿用脱贫攻坚架构,从县指挥部、乡镇工作团到村第一书记,体制机制暂时不变。”六盘水市阿戛镇长宫熙说,脱贫攻坚只是画上一个逗号而非句号,如何谋划乡村振兴,基层干部依然任重道远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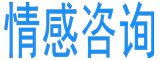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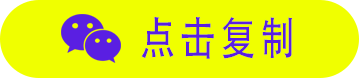




评论列表
我朋友咨询过,还真的挽回了爱情,现在两人已经结婚了
发了正能量的信息了 还是不回怎么办呢?
可以帮助复合吗?